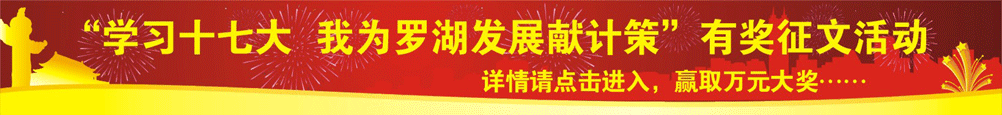
| 诚信纳税在我心 | |
| 作者:赖海群 | |
四年前,那时我未上大学,有一个故事至今还记得。 一天中午,作民办教师的父亲到家脸上挂着难得一见的喜悦神采,他习惯的那只黑包被他夹得紧紧的。一到家,他就把母亲拉进房间,“喀嚓”一声反锁了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悄悄地贴在门上听。里面喜悦的声音是父亲的:“转为公办教师的申请批下了,以后要加工资了,还补了一笔钱,有一万多块呢!”母亲的声音格外显露出兴奋:“哎唷”这么多钱哪!随后是“嘶啦”一声,看来母亲拉开了包的拉链,这会正在数着那一沓钞票呢。我敢肯定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父亲的音调低了几度:“不过,这些钱要交个人所得税,”母亲还没从刚才的兴奋劲中缓过神来:“这么说这些钱还指不定是我们的呢。为啥补给你的钱还要交还一部分给公家?不行,没这理!”母亲的脚步声“嗒嗒”地一路跳起。我一溜烟地躲开。门开了,母亲气呼呼地走出来,抛给紧跟在后面的父亲一句话:“我就不明白这理!”父亲耐着性子说:“国家依法征税也是为老百姓办事,将钱集中起来修路、办学校。如果没有学校,我哪有饭碗端着?咱家的孩子也没书读啊!”母亲的嘴唇动了几下,神情透露出她的立场有所动摇。父亲接着说:“咱们从来不坑人,邻里之间相处得这么好,人家还不是图咱们讲信用吗?”母亲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我,又看了父亲一眼,没再说什么,去张罗午饭了。 这件事过后好久,我才知道父亲第二天便到镇税务所交了那笔他认为应该交的钱,用的还是那只黑皮包。 儿时的记忆被为人师的父亲的殷切教诲所填充,父亲为人耿直、诚实。虽然这给他招来了不少责难和嘲讽,但他并未使屈服于世俗。他时常乐呵呵地说:“我半夜不怕鬼敲门,活得坦荡荡,这就行了。”四年以后,我来到繁华的广州读书。都市的浮躁没能冲洗掉一个农民的儿子身上特有的纯朴和真诚。 1 当月每个月从学校领取34.62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我对税收就又多了一份虔诚。 如今,“诚信”这个词被写进了我国《公民道德素质建设实施纲要》。可见,无论是对于纳税这社会生活之一角,还是对于个人立身处世、国家治国安邦,诚信都是重要的、必要的。我们这群大学生是社会的“预备公民”,很快也是纳税人了。而能诚信纳税则是考验我们一块试金石。 我能够写出这些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亲的影响。父亲并不高大的身躯在我脑海中化成的伟岸形象一直提醒着我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做事。明年,我就要毕业了,跨出校门、走进社会。我坚信自己也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父亲式”的个税纳税人。 弄虚作假的单位我绝不会跨进他的大门,偷税漏税的单位我也会在其门前止步。 黑龙江商学院的毕业生刘士泉,毕业四年多因不肯做假帐而换了四个单位。我也会这样,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因为父亲说的那句话还经常在耳边响起:“活得坦坦荡荡,这就行了。” |
|
| 观看次数:79 发布时间:2007-12-4 17:01:13 |